防疫史话(三)
按:为配合全民抗疫阻击战,介绍有关历史知识,中国煤矿文联与煤炭工业文献委共同组织防疫史话专题,从吴晓煜《瘟疫纵横谈》(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)选取部分文章,陆续在中国煤矿文化网和煤炭史志网上推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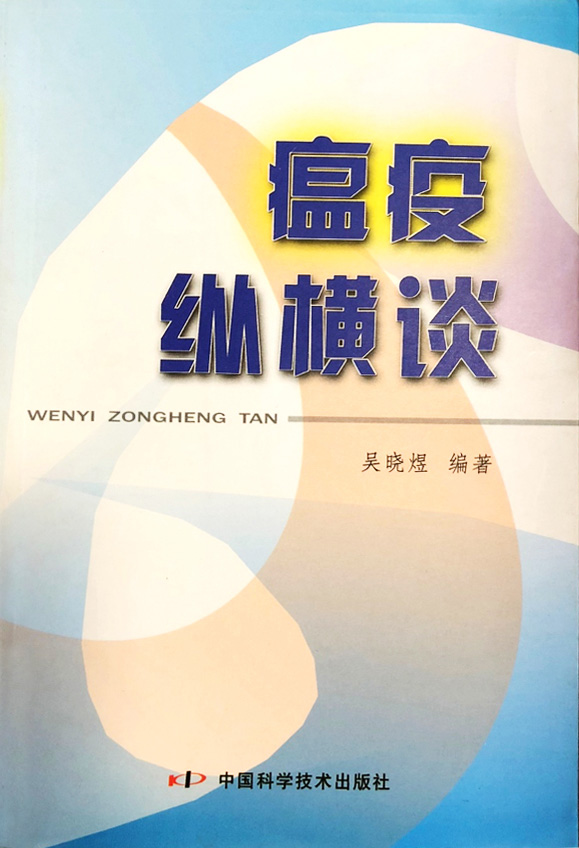
曹雪芹爱子夭于天花
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,他的巨著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,及于我国古典小说登峰的地步。直到今天,不仅中国人喜欢读《红楼梦》,连外国人也喜欢。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读它、研究它,有的埋头红学,终其一生。然而,对这部深奥的伟大作品,“谁解其中味”?
大家都知道,我们所看到的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,上面虽写曹雪芹著,但又有高鹗续。即他只写就了前八十回,而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。曹雪芹是一个才华横溢,学识出众的人,为什么不写完而半途停辍呢?为什么会出现砚脂斋所评“书未成,芹为泪尽而逝”的局面呢?原来,这与他的爱子染患天花而天折有较大关系。
曹雪芹的八十回《红楼梦》是在北京西山写就的,此时他贫病煎熬,穷困到了极点。有人讲他“作书时,家徒四壁,一几一杌一秃笔外无他物”。有时无钱买米断炊,有时连纸都不够用,只好把皇历拆开,写在历纸背面。他愁困著书,以泪洗面,泪透粗纸,可以说是“一把辛酸泪”,“字字句句皆是血”。
然而,最致命的一击,则是他的爱子天折。他的妻子已于多年前逝去,后虽续一才女,终非原配。他有一子,为前妻所生独子,十分可爱。由于孩子失去亲母之爱,雪芹对这个亲骨肉,格外疼爱怜惜,唯恐呵护不周。就是这样一个掌上明珠,却在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因天花不幸结束了脆弱的生命。
这一年,京城天花盛行,痘疹延祸,成千上万的小孩因天花而天折,造成一幕幕令人心悸的惨剧。据曹雪芹的好朋友敦诚所记“燕中痘疹流疫,小儿殄此者几半城,棺盛帛裹,肩者负者,弃走道左无虚目”,“途次见负稚子小棺者,奔走如织”。他的朋友家中小孩子夭折之事多有。就是这个敦氏家中也是五口遭痘灾而殁,“一门内如汝姑、汝叔、汝姊、汝兄,相继而殇,吾心且痛且恶,竟无计以避”,“即以目睫未干之泪,续之以哭”。这一年的八月,曹雪芹爱子也不幸染上天花。他哪里有钱给孩子治病,结果孩子在父亲无无力的眼底下,永远离开了他。
天花夺去了爱子的生命,使曹雪芹受到致命的打击。《红楼梦)又如何能写得下去。此后他病了,倒在床上,根本没有医药,朋友时而些许小助,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病情日甚一日,终于在当年的除夕,家家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,凄惨悲怆的曹雪芹到地下看望他的爱子去了。
我想,曹雪芹如果不是在贫病、痛失爱子的一连申重击之下,说不定还可以多活几年。那样的话,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红楼梦》可能就是曹雪芹写的全本了。
(2003年6月28日)
六世班禅因天花病逝于北京
对于西藏的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,大家是不陌生的。他是四喇嘛教格鲁派(黄教)的两大活佛之一(另一为达赖喇嘛),其地位仅次于达赖。班,梵语意为精通五明的学者;禅,藏语的意思是大;额尔德尼的满语意思为宝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在清顺治二年(1645年),以特硕特蒙古固始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罗桑却吉坚费为班禅,此人即班禅四世(前三世都是追任的)。到了康熙五十年(1713年),清政府“以班禅为人安静,精通经典,勤修贡职”,正式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,从此确定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。此后历世班禅转世,须经中央政府册封,成为量制。
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,六世班禅额尔德尼(名为罗布藏巴物垫伊西)为了提前给清高宗(即乾隆皇帝,生于1711年)庆祝七大寿,故向清政府呈请,“请祝七旬万寿”,经皇帝批准而东行祝寿。清廷对六世班禅的朝觐祝寿活动十分重视,接待规格宏大,比照顺治九年(1652年)达赖朝觐的先例,“迎护筵宴诸礼概从优异”。
为了迎接班禅六世的到来,乾隆帝命令在承德避暑山庄为他修建了行官,即须弥福寿之庙。须弥福寿是藏语札什伦布的汉译,此庙是皇家在承德建造的最后一座寺庙,位于避暑山庄之北,完全仿照班禅六世在日喀则所居住的札什伦布寺建造,故又称为班禅行宫。这里的“妙高庄严”殿是班禅的讲经之所,“吉祥法喜”殿是其下榻处,又称住宿楼。此庙北端的山巅上建有7层的万寿塔,寓七十大寿之意。
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八月,班禅六世“在热河祝嘏,至京居西黄寺”。班禅六世居于西黄寺(地处北京朝阳区黄寺大街)胡同,乾隆皇帝热情接见了他,对其十分尊重,礼遇有加,听他讲经并向他“颁赐玉印玉册”。
然而不幸的是,班禅六世在北京染上疾病,且病情严重。他得的是什么病呢?经御医诊断,是为天花,称为“痘”。由于当时对治疗天花根本没有什么好办法,不久便逝世了。据《清史稿》第525卷“藩部传”记载,六世班禅“以痘圆寂”。一代受人景仰的宗教领袖,本来是乘兴而来,却因染上天花而逝,这真是天大的不幸。如果班禅六世不是染上天花,亦或当时医疗条件可以治愈,我想西藏宗教历史有可能与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。
班禅六世因天花去世后,清政府于两年后,任命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为英藏办事大臣,护送其舍利及金龛回藏。并于西黄寺后楼前建衣冠石塔,用精美汉白玉石砌成,称清净化域塔(有“清静化域塔记”)。这是清代佛塔建筑艺术上的杰作。
另外,比较巧合的是,在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清廷曾命御史钟申保等带着朝廷文书请班禅五世来京。当时对方以班禅未出痘无法来京为由未能成行。
(2004年1月24日)
明景泰年间大灾大疫并行
明代宗朱祁钰即景泰帝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,当政期间内优外患交织,使朝政动荡,仅仅当了七年皇帝就一命鸣呼了。可以说他这个皇帝没有一天是顺心的、安宁的。
然而令国人心焦的是,这七年之内,各地灾荒之报如雪片向朝廷飞来,不是水灾就是旱荒,不少地方颗粒无收,百姓举家外出讨饭,流民遍地。如景泰元年(1450年)三月,直隶大名、顺德、广平三府饥民大增,不得不动用临清的广济仓,发粮赈济;是年五月,保定府饥民大有,只得从德州调粮;当年十二月,大同灾情又告急,各城军民乏食”;景泰二年(1451年)初,广平、大名府再次告急;景泰三年(1452年),不仅江西有大饥,而且南直隶、河南、山东等地水灾严重,无数灾民“流移趁食,在在有之”;本年八月,徐州又发生大饥荒,“饥民数多”,连官储预备粮都发光了,已无粮可调;景泰四年(1453年)山东、河南、风阳屡年荒饥,“民多流徙趋食”;景泰五年(1454年)江西建昌,湖北武昌、汉阳,湖南衡阳又生大灾,居民病饿而死者无计其数;景泰六年(1455年),江西、江苏相继报告灾情严重;景泰七年(1456年),陕西潼关、直隶、天津以及江西各府县都发生各种灾害,死者成千上万。真是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饥民无食,国无宁日。
但是,祸不单行,有灾必有疫,大灾必大疫,灾情与疫情并行而来,交相作用,恶性循环,这是一个规律。在景泰年间也是如此,大疫也跟着灾害而来,肆虐平民,戕害百姓,其后果也是触目惊心的。这里举例加以说明。
据明《英宗实录》卷213记载:景泰三年(1452年)二月,江西黄宜县发生严重疫情,一县之内死亡者多达4600余人;景泰五年1454年)二月,据巡抚江西右金都御使韩雍奏报,江西建昌府各县大疫流行,共死亡8008人;又据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叶峦奏报,武昌、汉阳二府大疫蔓延不止,共死亡1万多人;又当年五月,据湖广衡州府奏报,该地“去冬今春雨雪连绵,兼以疫疠,本府所隶州县人民死者一万八千四十七口,冻死牛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五只”(事见《英宗实录》242卷)。这正是,破屋又遇连天雨,灾之害已甚,又连之疫害。
可是,上述所举还不是最严重者。到景泰七年(1456年),灾疫交加,肆相为虐。是年十月,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报告;“江西各府县地方积岁薄收,人民缺食艰难。已委官勘实,饥民六十五万余口,共支官仓米谷三十九万余石赈济”。这六十五万饥民,加之瘟疫横行,那些嗷嗷待哺者、染疾待毙者,真是无望和悲惨到极点。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!
还有更甚的疾疫惨状。据湖广黄梅县当年十月奏报,“境内今春夏瘟疫大作,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,计三千四百余口;有全家灭绝者,计七百余户;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,人惧所染,丐食则无,假息则无所”,“悲哭恸地,实可哀怜”!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疫灾祸害之巨大,而且还可以看出,中国的老百姓在无望无助的绝境之中,他们的命运是何等的凄惨!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何等的严重!面对这样的惨状苦景,有谁能不为之扼腕悲愤呢?
当然,明王朝宫廷以及有关地方官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,诸如开仓放粮、减免赋税、施以药物、掩埋尸体等。但是这些措施又是那样的无力,再加上个别污吏从中贪索,缺乏应急的必要财力与组织措施,必然使灾情和疫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。不然,仅仅一个省份何以出现几十万的讨饭流民,一个州之内何以有成千户的全家灭绝情况发生?
(2003年6月1日)
明代北京的几起大瘟疫
应该说在明代前期,首都京城的防疫措施还是可行和有一定效果的。由于朝廷的重视,加之京畿要地是皇帝及中央政权办公的地方,医疗机构相对其他各省要健全一些,各方面官吏也比较注意疫情监控,因而从明初开始,至成化初年(1465年左右)这一百多年间京师很少有较大规模的疫情报告。
但是,到了明宪宗的成化年间,以至整个明代后期,就发生了若干起疫情爆发的事例。笔者根据《明实录》的记载,简要介绍发生于京城的较大疫情。
成化七年(1471年)三月,顺天府尹李裕等奏报,“顺天八府比岁民饥,流民颇多”。在饥荒之后,京城紧跟着发生了瘟疫大作的事件。到了五月,这位府尹向朝廷奏报了京师瘟疫的情况。他说:“今日京城饥民疫死者多。”看来这次是灾荒与瘟疫并行而虐,灾疫交加。京城饥民又染上瘟疫,真是无路可走,只有等死而已。那么是怎样救灾防疫的呢?据他讲,一是向户部“借粮赈济”;二是“责令本坊火甲迷其死者”;三是,也是荒唐可笑的,则是他“择日斋戒,诸城隍庙祈祷灾疠”。看来这位府尹是一个救治瘟疫不太得力的京城官员,就凭他到城隍庙“祈裤灾疠”这一点,可以想见其结果如何。更可笑的是,比他更糊涂的明宪宗朱见深竟然同意了他的做法。
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,京城又发生规模很大的疫情。据明《世宗实录》409卷记载,是年三月“都城内外大疫”,“时疫大甚”,染疫而病死者无计其数,史书上讲是“死者塞道”从“大疫”、“大甚”、“死者塞道”等寥寥数语,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疫情是多严重。然而,明廷的救治措施却不能说是很到位。而明世宗朱厚熜接到奏报后,“谕礼部曰:……朕为之侧然”,仅仅是表示悲伤同情而已。
万历十五年(1587年)五月,北京城又发生较严重疫病情况。大学士申时行等奏报:“兹者天时亢阳,雨泽鲜少,诊气所感,疫病盛行。”因此,他们请求皇帝“敕礼部札行太医院多发药材,精选医官,分别于京城内外给药病人,以广好生之德”。明神宗对这次京城疫情比较重视,第二天便向礼部发出谕示:“朕闻京城内外灾疫盛行,小民无钱可备医药。尔部便行太医院,精选医官人等,多发药材,分投诊视施给,以称朕救民疾苦之意。”他还令礼部“每多家给予银钱一次”。至于每户疫病人家发给多少钱,则未作明示。看来明代的防疫工作由礼部负总责。
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京城不仅比年发生大旱,又复遭水灾,接着又发生瘟疫。据《神宗实录》493卷记载:“给事中韩光枯比岁畿辅旱荒,去年复遇大水。今流离载道,行路酸辛,又多苦疫疠,竟委沟瘠。”这次灾疫接踵而至,对京城老百姓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居民流离失所,贫病交织,许多人就好端端的倒在了荒沟坡旁,永远也站不起来了。根据这种形势,这位给事中请求朝廷,对“被灾之地或发币金,或发廪米,布令所司招抚流移,计口赈贷”。此外他还向皇帝报告了救济京城灾民、病人的粮米和治疗费用入不敷出的窘况,对此只有多发钱米一法,这样才可以“全生灵之命,回天地之心,收既散之民,消意外之衅”,以防各种乱子发生。应该说他的奏报以及建议是完全可行的。而且他把救灾治疫与维护社会稳定联系起来,也是有见地的。
崇祯五年(1632年),京城又发生疫情,而且波及到狱中人犯。据《崇祯长编》59卷记载,本年五月,刑科左给事中陈赞化奏报:“时值炎热,瘟疫流行,秽恶之气,传染易遍,即都城狱内几至千人,病至无日不报。”就连监狱内的传染病犯人就多达千人,而且染病之例“无日不报”,说明了京城的瘟疫流行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。
(2003年6月1日)
道光元年北京的一次大疫
清道光年间(1821-1850年)国运日渐衰微,虽有大清王朝的外在威风,但内里缺乏改革与开放意识,逐步落后于外人。与此同时,一些洋人打起到中国掠夺的算盘。以侵夺中国人民利益为目的的鸦片战争就发生在道光二十年(1840年)。
在这种经济、政治背景下,瘟疫也似乎喜欢在道光皇帝(清宣宗)执政时期充分进行表演。据《清史稿》一书记载,从道光元年(1821年)至鸦片战争(1840年)爆发的20年间出现的瘟疫蔓延就有14次之多,平均一年多一点就发生一次。这些瘟疫分别发生于道光元年、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六年、七年、十ー年、十二年、十三年、十四年、十五年、十六年、十九年和二十年(1821年、1822年、1823年1824年、1826年、1827年1831年、1832年、1833年、1834年、1835年、1836年、1839年、1840年)。而北京城在道光元年(1821年)就发生了大瘟疫。
据《北京市卫生大事记》一书转引的一条资料介绍:“道光辛已(1821年)春夏间,瘟疫流行。始自闽、粤、江、广,日迟于北。七月望后,京中大疫,日死者以千数。其疾始觉胫痛,继而遍体麻木,不逾时即死。治者以针刺舌腭逮紫血出,再服藿香正气丸,始得无恙。然死者多为里巷小民,士大夫罕有染者。”
从这段记载来看,这次瘟疫是始于外省,然后传入北京的。这种分析可能是有道理的。因为,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这一年北京的周边地区,如任邱、新乐、通县、济南、滕县、唐山、滦州、内邱、望都、曲阳、武强、青县定州、清苑、巨野等地或“瘟疫流行”,或发生大疫,或“时疫大作”,可以说北京是处在周边地区所发生瘟疫的包围之中,北京这个交通、经济中心,必不可能免于瘟魔之袭扰,而发生大疫则是十分必然的事情。
北京这次瘟疫实属大疫。值得注意的有三点:一是,死者甚多,后果十分严重,“日死者以千百数”。二是,因染疫而死者“卒多里巷小民”,这是很符合事实的。因为平民贫户,卫生条件差,生活异常艰辛,有病无钱请医买药,得不到及时的救治,这样时疫必然会在贫民区中首先蔓延,造成大量贫民死亡。三是,从症状来看,死亡速度极快。“其疾始觉胫痛,继而全身麻木,不逾时即死”。还有一个当时流传很广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情况。有个叫罗承光的刑部侍郎,“年逾六十,身体素健”。他早晨来署衙上班,当听说关于瘟疫的事情,根本不相信,并“力斥其妄”。然而不幸的是,过了一会儿,他本人也染上瘟疫,“逾时觉不爽”。于是回家休息,刚进家门就倒地死掉了(乘兴而归,及抵家已卒矣)
那么,这种瘟疫具体是什么病呢?清人王土雄《重订霍乱论》中讲:“直省此证大作,一觉抟筋即死,京师棺木卖尽,以席缠身而葬,卒未识为何证者。”《医林改错》一书也讲:“京师瘟毒流行,死者无以为殓。”有人在瘟毒后注为霍乱。我不是医务工作者,但从上述说法来看,霍乱的可能性很大。
应该说,道光皇帝对于这次时疫是比较重视的,采取的措施比较及时。他在当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就向内阁下达了明确的谕示
昨因京城内外时疫传染,降旨著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、五城,分设药局、棺局。著都察院堂官于五城地方,拣派满汉御史各一员,不时自行查访,奉行不力者,即行据实参奏。
看来这位皇帝对老百姓还是关心的。设药局以分发药佴,为民疗疾;设棺局以殓尸,防止病尸传染,以安定民心;令都察院派员进行督促落实,对执行不力者进行惩处,这些都不失为有效的举措。但是,这些措施是否在各级官吏、各个环节都能得到落实,那就很难说了。不然,这次瘟疫不会造成那样的严重后果。
(2003年12月22日)
煤矿文联动态
-
2024年7月5日,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、中国煤矿文化... [详细]
-
4月18日至19日,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第六次会员... [详细]
- 中央社会工作部召开全国性行业协会…
- 万福迎春·中国煤矿文艺志愿服务走…
- 第十届全国煤矿文化干部高研班正式…
- 2023年《阳光》杂志、全国煤矿文化…
- 中国艺术报:“一团火”的矿山追梦…








账号+密码登录
手机+密码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